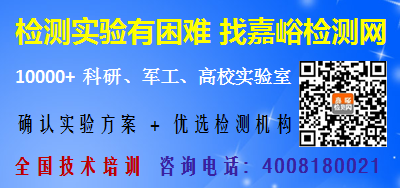2.2.3 免疫學方法
免疫法[28]是從二噁英的致毒機理出發,當二噁英類化學物質與細胞接觸時,首先會與細胞內的芳 香烴受體相結合,然后轉移到細胞內,二噁英類化合物在體內和芳香烴受體結合,結合的緊密程度決 定其毒性水平,因芳香烴受體是二噁英類化合物發揮毒性作用機制的基礎物質,它的被活化程度與該物質毒性一致。用芳香烴受體法測定的是二噁英與芳香烴受體的結合程度,通過芳香烴活化程度的測 定來間接的表達二噁英的毒性當量(TEQ),芳香烴受體是 TEQ 的生物學基礎,所以用芳香烴受體法更 適用于健康評價[1]。2002 年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規定把酶免疫分析法用于土壤中的二噁英測定[19]。 常見的方法有 EROD 細胞培養法、熒光素酶法、EIA 酶免疫法、時間分析熒光免疫法(DELFIA)和通訊 基因檢測法等,DELFIA 是目前最先進的免疫方法[29-30]。免疫法具有簡便快速的優點,但是抗體難于 獲得且不能檢測所有同系物,還可能出現假陽性和假陰性問題,適合于作現場研究,特別是需要得到 快速結果的場合。
2.2.4 其它方法
電化學方法用于研究二噁英的電化學性質也有報道,日本學者用電解的方法電解二噁英實驗獲得 成功。二噁英的主要成份氯經電解后,在溶液中形成氯化物或氯離子,該方法簡單,使用電壓低、生 成物的毒性較弱,如進一步電解,可達到無毒化,因而具有廣泛應用的可能性。日本大阪大學和大阪 激光技術綜合研究所開發了激光快速測定的儀器來檢測二噁英,利用低能量的激光將食品中的二噁英 變成氣態,然后再利用高能量的激光讓二噁英分子帶電,最后根據這些分子在測試裝置內移動的時間 就可以計算出食品中二噁英的含量[31-33]。
3 結論與展望
隨著二噁英的毒性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越來越受到科學家的重視,而傳統的分析方法在選擇性和靈 敏度上遠不能滿足對現代食品質量監測的需要。因此,二噁英的分析方法面臨著重大的技術挑戰,建 立快速、準確、靈敏的檢測方法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化學分析法、生物學方法、免疫學方法及這 些方法的聯用技術仍然需要完善與創新。直接實時分析-質譜(DART-MS)技術自 2005 年發明以來因具 有快速、實時、綠色的優點而得到迅速發展,已經作為一種新的分析技術被快速的應用于藥物發現與 開發、司法鑒定、材料分析等領域[34-39]。根據需要改進 DART-MS 技術,可以將該方法運用到食品中 二噁英類的檢測。
參考文獻
[1] 周莉菊, 馮家滿, 趙由才. 工業安全與環保, 2006, 11(32): 49-51.
[2] O Sorg, M zennegg, P Schmid, et al. The Lancet, 2009, 374(9696): 1179-1185.
[3] 王連生, 鄒惠仙, 韓朔睽.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4] 繩珍, 關江, 曹先仲, 等. 山東化工, 2008, 37(7): 12-14.
[5] T Ishida, E Naito, J Mutoh.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 2005, 51(4): 410-417.
[6] 仲維科, 李翔, 李淑娟. 檢驗檢疫科學, 2004, 14(4): 13-15.
[7] 徐旭, 嚴建華, 池勇, 等. 能源與環境, 2003, 21(6): 24-27.
[8] 廖濤, 熊關權, 林若泰, 等. 食品與機械, 2008, 24(4): 153-165.
[9] 程永友, 王迪, 王慧文, 等. 中國畜牧獸醫, 2007, 34(6): 71-75.
[10] T. Gouin, D. Macky, K.C. Jones, et a1.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4, 128(12): 139-148.
[11] B R Stanmore. Combustion and Flame, 2004, 136(3): 398-427.
[12] 劉靜, 崔兆杰, 許宏宇, 等. 山東大學學報(工學版), 2008, 38(4): 116-122.
[13] 趙毅, 張秉建, 賀鵬. 電力環境保護, 2008, 24(6): 44-47.
[14] 金軍等主編. 中央名族大學出版社, 2006.
[15] 佟璐, 劉然, 肖明乾, 等. 食品研究與開發. 2000, (21): 38-39
[16] K Srogi. Enxiron. Chem. Lett, 2008, 6:128.
[17] 姜欣. 皮革化工, 2006, 23(4) : 39-42.
[18] E J. Reiner, R E. Clement, A B. Okey, et, al. Analytical and Bioanaltical Chemistry, 2006, 386(4): 791-806.
[19] 王承智, 石榮, 祁國恕, 等. 環境保護技術, 2006, 32(2): 30-33.
[20] 王承智, 胡筱敏, 石榮, 等.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06, 16(5): 135-140.
[21] 鄭明輝, 楊柳春, 張兵, 等. 分析測試學報, 2002, 21(4): 91-93.
[22] 程永友, 楊曙明. 中國飼料, 2007, 16(13): 36-38.
[23] 孫晞, 歐仕益, 彭喜春. 環境與職業醫學, 2007, 24(2): 218-221.
[24] 李瑩, 金一和. 環境與健康雜志, 2004, 21(3): 168-169.
[25] H Takigami, G Suzuki, S Sakai. Biological Respnses to Chemical Pollutants, 2001, 27(6): 87-94.
[26] M S. Denison, E F Yao. 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sics, 1991, 284(1): 158-166.
[27] S X, L F, W Y J, et al. Toxicological Sciences, 2004, 80(1): 49-53. [28] 彭潔, 高洪. 中國畜牧獸醫, 2009, 36(12): 36-41.
[29] 吳廣楓, 孫晨星, 石英. 食品科技, 2007, 30(11):23-28.
[30] K Komura, S Hayashi, I Makino,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chemistry, 2001, 226(2): 107-117.
[31] 袁倬斌, 李珺. 分析化學, 2001, 29(10): 1222-1227.
[32] 丁鋒. 糧油食品科技, 2006, 14(3): 51-52.
[33] 馬靖, 丁蕾, 顧學軍, 等. 中國激光, 2005, 32(9): 1202-1206.
[34] C H Wen, Z Jian, L M Biao, et al. Journal of Mass Spectrometry, 2007, 42(8): 1045-1056.
[35] C Petucci, J Diffendal, D Kaufman, et al.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7, 79(13): 5064-5070.
[36] H Jin Kim, Y Pyo Jang. Phytochemical Analysis, 2009, 20(5): 372-377.
[37] L Vaclavik, T Cajka, V Hrbek, et al.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09, 645(1-2): 56-63.
[38] B E, Dane AJ, T S, et 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10, 58(8): 4617-25.
[39] L M biao, H Bin, Z Xie, et al. Analytical Chemistry, 2010, 82(1): 282-289.